毛泽东读马列著作
逄先知

毛泽东是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进行探讨、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便终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地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来读。
为解决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
1920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1926年已经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但是问题不在于读了这本书,可贵的是,毛泽东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革命问题,指导中国的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但是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啊!在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的时候,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毛泽东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也是使他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当年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亲眼看到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感人情景。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一位忠诚的老革命家。在一次访问中,她对我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听了这段生动的回忆,使人对毛泽东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的精神,感佩不已!另据吴黎平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
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恐怕也是列宁的著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喜欢读列宁的著作,还因为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毛泽东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在列宁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著作,又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当然不只是这些)。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两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这两本书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从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毛泽东特别重视列宁的这两部著作,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
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当时毛泽东阅读、圈画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现在保存在毛泽东故居的已经为数不多了,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多卷本,苏联出的中文版)、《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收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苏联出的中文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圈画的马列著作,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某些思考。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也都是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阅读的。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翻开书一看,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画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画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重温列宁这部重要著作。他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一日。”中宣部在6月1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教育干部,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据我看到的,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评论。(这里顺带澄清一个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所谓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那是误传。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是作过批注,但不是“文革”中流传的那个本子。)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该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五条,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讲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则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这些批注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论点。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讲话中得到了充分展开。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毛泽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并没有全盘肯定斯大林这本书,然而他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他在读这本书时阐述的一些好的观点,至今还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干部
毛泽东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干部,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在延安整风中,为了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亲自规定高级干部都要学习《“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他提议整风之后,组织人力大量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当时他说:我们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如果读通了这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我们党就武装起来了,我们党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9年,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十二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七届二中全会。由毛泽东起名的《干部必读》十二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从思想上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为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央决定全党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九至十二章。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准备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说,《毛选》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大意)。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学习苏联,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我们从苏联经验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但也有消极的一面。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苏联经验缺点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在总结我国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不同于苏联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在1958年“大跃进”出现严重失误的时候,干部中产生了某些混乱思想。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问题作出布置。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高中级干部读书。他认为,原来提出的目录,哲学书开得少了,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他还提出,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他说: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过了不到一个月,8月4日,毛泽东专为印马列著作大字本问题写信给周扬,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使每本减轻重量。毛泽东对印大字本关照得如此细密周到,是为了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发展马列主义,创造新的理论
毛泽东重视阅读马列著作,但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反对死读马列的书,生搬马列主义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他曾说过:“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
关于应当用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今天读来仍很受教益。他说;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后,又在1965年12月重新提出写序问题。他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我也随着他们去了,还给毛泽东带去三十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加上别的一些书,装了两大木箱。毛泽东特别提醒,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
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总的来说他又不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个别论断束缚。他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大胆地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他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也曾经为开创一条中国式的道路进行过思考和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凝集着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光辉的思想,成为我们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他本人主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个任务,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又发生过失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经验,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力求创造出新的理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介绍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情况后,我想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毛泽东一生坚持读马列著作,并且一再号召全党学习马列著作,为什么自己在晚年却犯了严重错误?我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又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因而对现实社会状况和许多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估量和分析。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脱离实际,主观专断,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出色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这是大部分时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就做出巨大贡献。他在晚年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甚至误解,则又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紧密结合活生生的现实,实行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从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经验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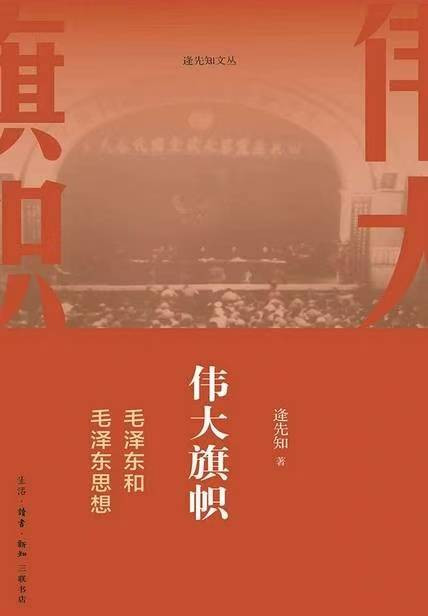
(本文逄先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出版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