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生命史、学术史、思想史的有机统一
生命史、学术史、思想史的有机统一
——评《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
全根先

按语:拙作《一代名师的学术报国路:评〈丽泽忆往〉一一刘家和口述史》一文于2021年8月12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光明网、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中工网、光明阅读、中国青年报、中国历史研究院、云南网、荆楚网、华讯网、秦都网、知乎、一点资讯、安防观察、中外好人网、360个人图书馆等多家媒体转载,可见大家对于名师和教育的期待和重视。由于《光明日报》发表时篇幅有所压缩,现将本文初稿发表,敬请批评指正!
记忆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功能,是认识与思维的必要前提。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说:“我们如果没有记忆底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自我;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记忆,这个社会就无法进步。社会记忆的本质是人类基于实践而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凝聚累积,是人类历史的连续性传承机制。在人类历史上,记录历史的媒介或手段主要有四种:文字、图像、实物和口头传统。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文字似乎一直是历史记录、文明传承主角。然而,口头传统其实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记忆手段。我们常说的“文献”一词,见于《论语·八佾》。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所谓“典籍”,即历代文献或典册、书籍;所谓“贤”,指见多识广、熟悉历史的贤人。历史通过贤人而被记忆、通过文字而得以记述,从而汇入人类历史长河。
历史归根到底是由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来书写的;如果历史都是由后人来书写,没有亲历者和见证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佐证,难免会有主观判断抑或杜撰成分。口述史学通过对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访谈,记录留存于他们脑海的历史记忆,不仅可以弥补现有史料之不足,还原部分历史真相,还能使概念化的抽象的历史叙述变得生动鲜活。另一方面,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作为一个自然的生命,其记忆如果不进行及时记录,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口述史所要做的工作,正是要抢救这些可能消失的历史记忆,使其成为可以保存和研究的历史文献。而在所有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中,个人以为,学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是人类文明自觉的创造者、记录者和传承者,是人类文明向新的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良好的表达能力,其口述文献更加弥足珍贵。我今天所要介绍的一部口述史著作《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可以说是一部内涵丰富、结构精巧、思想深邃、引人入胜的口述史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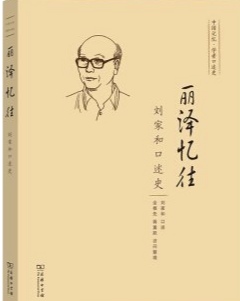
寓宏大历史于生命史之中
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一般情况下,都会经历重大社会变革,从而在其个体生命中折射出时代气息。刘家和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与常人不同的是,刘先生以90余岁高龄,不仅经历的事情可能比常人更多一些,而且作为历史学家,对于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情感体验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通过他所经历的事件或所接触的人物,可以感受到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可以说,刘先生口述史中所提到的事件或人物,既是真实的,又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选择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刘先生出生于南京市六合区,那时六合还是南京附近的一个县城。可是,由于紧邻大城市,交通比例便利,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正悄然地改变着他家乡的社会生活。刘先生在回忆说:
那个时候外国经济已经渗透到六合。煤油也可以通过船再运到别的镇上卖,也可以运到安徽其他地方卖。外国经济进来了,很快就有电灯了。当时,电灯不是二十四小时都有电的。那时不叫电厂,叫电灯厂,白天没电,天黑了来电,点电灯,到十二点就停了。生活中已经有很多变化。六合到南京之间也有了轮船。到南京的轮船来回不是一班,每天至少有两班对开,但是还没有汽车。(《旧时景物》)
刘先生在这里所讲的,正时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缩影。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做出了巨大牺牲,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刘先生才三岁,尽管有一点模糊记忆,却什么都不懂。然而,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刘先生已经上小学,有了深刻印象。不仅如此,他还亲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小小年纪就遭遇生命危险。刘先生回忆说: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我并不在城里,但是我知道一些情况,因为我们在南京的下游江边上。我自己没有到江边去,我知道这个船过来,因为天很冷,为了过江,日本飞机轰炸得很厉害,很多人抱着一块木板过江。有的人更惨,就是抓住一捆救命稻草,急得抱着一捆稻草过江。你说,这么冷的天,稻草到江中间就散了,许多人都这么被淹死了。(《避难竹镇》)
1938年农历4月27日(公历5月26日),那时候一般人都记农历,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日寇轰炸,异常悲惨。我们在路上跑时,飞机一直轰炸街道,子弹密集地扫射下来。我们往家跑的那条路是从南到北,路上不是我一人跑,孩子们都跑,还有大人啊!好多人就这样死在路上,被机枪子弹打中。那时,江南春天的雨刚过,初夏时节,不是有句话:“梅子黄时日日晴”吗?土地比较干。机枪子弹打到地上以后都冒烟,我就眼看同学有一些被打死。(《日寇轰炸》)
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形象?对此,有不同的文献记载,也有不同的解读方法,知识分子本身也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刘先生的回忆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具体形象。其中,汪海秋先生就是比较典型的民国时期小知识分子形象。汪先生颇有才学,家境贫寒,却能怡然自得,安贫乐道。刘先生回忆说:
先生家在六合算是一个大家族。他的儿子是“国”字辈排行,大儿子叫汪寿国,也可以叫汪国寿,排行放后面。他的儿子很聪明,可是读不起书,送到一个绒布店去当学徒了。因为到布店里当学徒,经常还能拿回来一点零钱,还能帮助养家糊口。他的二儿子叫汪同国。这个更可怜了,他就去挖野菜,因为家里连买菜钱都困难。六合这地方,蚊子多的不得了,可是他家的蚊帐都是破的,根本就不能挡蚊子。所以,汪先生家生活费用中很多还要去买蚊香。可是,汪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仍然怡然自得,安贫乐道。(《汪海秋师》)
唐君毅先生是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当年唐先生在江南大学任教,他和妹妹唐至中先生对刘先生都十分器重,关怀备至,对刘先生的学术和人生有重要影响。刘先生回忆说,1948年3月15日,学校组织一次学术讲演,唐先生作为教务长,坐在前面指挥。讲演安排在公益中学简陋的礼堂里面,讲着讲着,忽然听到一片倒塌声,现场顿时就乱了。讲台上的先生们因为离前面的门比较近,很快就出去了;可是学生们一下子就拥挤起来。这时,唐先生却不走,他穿着大褂在那里指挥,劝同学们要镇定,有秩序地走。刘先生走到讲台底下,看到唐先生已是满头大汗。直到倒塌声停止了,有一个工人过来帮忙,他才出来。通过这件事情,这么一个细节,刘先生向我们传达了唐先生的高尚人格。刘先生说,唐先生讲的虽然是西方哲学,可他践行的却是王船山的儒家精神。
刘先生讲的另外一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唐先生的高尚人格。当时,刘先生的同学李赐因生活困难,由唐先生资助上学。唐先生写字比较潦草,李赐在唐先生讲课时,帮他抄讲稿。唐先生已经资助李赐生活费了,请他抄稿子,别人可能以为这是义务的,可唐先生照样给李赐付抄稿费。有一次,刘先生与李赐在唐先生家吃饭,就问唐先生,为什么还要给他抄稿费,是不是有点过了?唐先生说:“刘家和,你以为我是资本家,在雇佣李赐吗?他是作为我的学生、朋友帮忙的,我当然要谢他了!”对此,刘先生回忆说:“唐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教育太大了!我这一生,对唐先生的那种临危不惧、视学生的生命重于自己生命,资助了还给报酬、说谢谢这样的为人,永远是值得我学习的。君毅先生在我心里就是道德榜样,到现在不能够变!”(《唐君毅师》)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很多。总之,通过刘先生的口述史,不仅可是窥见中国社会和发展变迁,还能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洗礼。

寓学术史于生命史之中
对于学者而言,学术史在其生命历程中自然非常重要。所谓学术史,不仅是学者本人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还包括其学术精神的发育和成长,学科或专业的发展线索。通过学者口述史,可以大致了解一个学科或专业的发展脉络。刘先生的口述史,将学术史寓于生命史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学者的成长过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变迁,特别是中国世界史学科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刘先生的学术启蒙于幼年时期,一开始进的是私塾。他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与其良好的传统教育、深厚的国学根基密切相关。由于天赋优异,他记忆力过人,背书很快。刘先生回忆说:
我背书比较快。那么,有什么秘诀没有?我就是尽可能地把意思弄懂。我知道,掌握典故越多越好。(《私塾启蒙》)
我读了《幼学》以后,就知道这些故事:“开镜香生京兆笔”。为什么是“京兆笔”?擅长画梅啊!“启窗花印寿阳妆”,说的是寿阳公主。这样就逐渐培养了我的兴趣。家里没人了,只有母亲和我,我就干这个。所以,对我来说,读古书我根本不怕,反而有一种强烈的兴趣。(《迷上对联》)
中学时期,时仰伯先生讲国文,就引起刘先生对词源学的兴趣。在江南大学时,刘先生听冯振先生讲文字学。冯先生讲《说文解字》,先讲《序》,然后讲部首,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讲。通过这个,刘先生知道了清代汉学家的一些东西。钱穆先生当年跟刘先生说,要研究先秦诸子,必须有清代学术作基础。经过时仰伯先生、钱穆先生、冯振先生的指导启发,为他今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先生回忆说:
我从冯先生那里知道,有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段若膺(段玉裁)等。这个对我以后学术研究,这都是配套的。钱先生跟我讲,你要搞清代学术。其实,要搞古代史研究,离不开清学,我对清代学术、小学几乎到着迷的程度。
冯先生是广西北流人,他把见(jiàn)读成(gàn)。下课休息时,我对冯先生说:“你把见(jiàn)读成gàn,这不是你的方言吗?”冯先生说:“刘家和,你可要记住,我说的正是古音。你要注意,以后知道这方言里头是中古音。”从那以后,我走到哪儿都注意听古音。(《冯振心师》,有删节)
因为江南大学办学方针有变,刘先生没有毕业,就转学到南京大学。到南大以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从同学刘永岳那里,知道了南大的历史,其实也是学术史。他知道当时史学界有“南柳北陈”,南方是柳诒徵先生,北方是陈垣、 陈寅恪先生。刘先生从柳诒徵说起,梳理了南大的学术传承。刘先生说:
柳先生十七岁考中秀才,以后就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上了三江师范学堂。那不是李瑞清创办的学校吗?李瑞清这人,我在江南大学就知道,他不是给无锡荣家写的字嘛!梅园那个楠木厅,就有李瑞清题写的字:“诵豳堂”。《诗经》里不是有《豳风》吗?这个在荣家老宅里。
李瑞清是何许人?他是清朝光绪年间进士,当过翰林庶吉士,后来外派,做过江苏修补道、江宁提学使。光绪末年,清朝政府就派他到南京来,组织筹办新式高等学堂,出任两江师范学堂校长,当时叫监督。柳先生呢,就是三江师范学堂李瑞清先生的弟子,后来又到江阴南菁书院跟缪荃孙先生学。
缪荃孙先生也是光绪年间进士。他是江阴人,张之洞在四川当学政,他已经中举了,就去帮张之洞,他们一起编纂《书目答问》。柳先生既是李老先生的学生,又是缪老先生的学生。李瑞清先生学问非常渊博,经学、小学什么都通。胡小石先生就是李瑞清先生弟子。(《拓展视野》,有删节)
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刘先生在其口述中,也为我们理清了一个大致发展线索。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翻译、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艰难探索过程。对此,刘先生在其口述中有多处表述。他说:
李(飞)先生讲的这本书还有一个中译本,何炳松先生翻译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炳松先生的《欧洲中古史》,我一看,这不就是鲁滨逊的《欧洲通史》吗?这是我们中国人写的外国史。实际上,谢兆熊先生讲西洋通史,就是讲欧洲通史。何先生学贯中西,研究浙东史学,搞中西比较。以何先生这样的情况,搞外国史,也还是拿鲁滨逊的书来讲课,这是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一个实际情况。
那么,鲁滨逊何许人也?鲁滨逊是做新史学的,他是美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很有盛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提倡新史学。梁任公先生也讲新史学,也是从这儿得到启发。可是,他为什么叫新史学?他是针对兰克史学说的。德国兰克史学,不是欧洲史学基本上以政治、经济、外交为历史主要内容吗?鲁滨逊就把这当作问题提出来,认为历史学应该包括其他学科。
可是,我觉得这对中国史学来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中国《二十四史》都有“志”啊!《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都是专门史,还有什么《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是不是?中国史学不存在这种歧视,这是从中国传统学术上讲。还有这个所谓的新史学,在当时已经不是新史学了。真正的新史学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我们国家面临的史学发展方向,一个是西方人搞的外国史学研究,解放前叫西洋史;一个是解放后向苏联学习,叫世界史。我们讲的世界史,其实是西洋史,西欧中心论。刘启戈先生翻译的《世界通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那里讲到被殖民国家历史,可是他加了个题目,《白种人的负担》。所以,这样的新史学中国人难以接受。(《助教初期》,有删节)
由此可见,刘先生的口述史,叙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经历,而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近代学术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寓思想史与学术史之中
在史学界,由于个人的学术素养和学术兴趣,历史学家大致可以分为偏重思想或偏重考据两类,而刘先生可以说是少有的两方面都有深厚造诣和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对于学术研究,刘先生曾提出“三大张力”:一是中西方比较研究的张力;二是哲学与语言学,深度与广度的张力(即两个“Philo”,Philosophy、Philology);三是“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张力。这“三大张力”,也是刘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经验总结,是在前辈学者的精神滋养下、通过个人努力而逐步形成的。在回忆唐至中先生讲国文课时,刘先生说:
《逍遥游》开篇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北海有大鱼,不知其几千里,你看多了不起!还有小蚁、麻雀、蜩与学鸠,这些很小,这就存在大和小的关系。小自以为很大,其实大小之间关系是相对的,你从什么角度看?庄子在其他地方讲:“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你看,大小是相对的,伟大或渺小都是相对的。
《逍遥游》其中有这样一段:“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有所待也。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你觉得自己能腾云驾雾,其实还是有条件的,你还是有所待的。鲲化为鹏的时候,鲲都要在浩瀚的大海里才能游;鹏为什么要能够背负苍天,由北冥到南冥,底下要有汽。所有的一切都渺小,都有待。(《唐至中师》,有删节)
唐至中先生对《逍遥游》思想的分析,对青少年时期的刘先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智慧的启迪。在江南大学时,唐君毅先生讲哲学概论,讲到斯宾诺莎、黑格尔,特别是讲黑格尔,使刘先生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他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他之所以能站在历史研究的最前沿,提出常人不易发现、不去思考的学术问题,都与他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有关。刘先生说:
我这一生对黑格尔的兴趣是君毅先生引起的。君毅先生说,斯宾诺莎讲过一句名言:规定即否定。斯宾诺莎认为,实体是无限的,不能有任何形状的规定,形状只存在于有限的、被规定的个别事物中,规定就是界限,就是对无限的否定。在他看来,作为样式的个别事物是有限的,当人们对一个具体事物作出某种规定、说它是什么时,同时就意味着把它和别的事物区别了开来,否定了它是另外的事物。
唐先生对黑格尔非常欣赏。黑格尔说的,有它的不足。黑格尔说,所有的规定都是否定,是对的;反过来说,所有的否定又都是规定。唐先生讲到这儿时,使我感到震惊。在斯宾诺莎看来,规定即否定,否定涵摄规定。不否定,规定是不清楚的。到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精神现象学》开始讲,纯粹的有立刻转化为无。对辩证法,我兴趣大,唐先生的教育作用大。(《唐至中师》,有删节)
在学术研究中,博与专的关系非常重要,两者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20世纪80年代,刘先生到美国访学,接触到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必要的张力》一书,对其学术思想颇感兴趣。刘先生认为,在学术研究中,的确存在张力问题。他说:
我从《毛传》《郑笺》里看到一些问题,看了孔颖达的书。孔颖达的书,有些地方可以深入下去,有些地方就不能,的确来不及。我是这么一个想法,库恩讲的必要张力,《中庸》里有,《孟子》里也有。《中庸》讲了三句话,其中最后一句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都是张力。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你只有在博学的情况下,才能发现问题,才能专。“博”这个字,实际上有两解的,《荀子》是有解释的。我曾经讲过,“博,大通也”。博,要大而通。你再看这个《修身》:“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眊”。这里就有张力。(《必要张力》)
历史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就是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过去我们常说,西方人是站在西方的角度书写世界史,充满了偏见,中国在世界史中没有地位,那么,我们中国学者写世界史,能不能做到客观?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西方中心论”,如何摆正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刘先生长期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说:
史学家能不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纯客观地书写历史?我记得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有句话。他说,现代人类最好能够放弃主观。人类要是能到月球上去看,就可以做到客观了。我看到这话,我就感觉,人类要是真到了月球上,就会站在月球的立场上来说话,不会没有立场的。人类对历史,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是无法消灭的史学家的主观。消灭史学家的主观,历史也就完了。不是讲张力吗?这头线一断,那头就完了。那头史实或者说史料一断,史学家就完了,没有研究对象了。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人的主观性,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统一历史观、统一思想,中国历史上也干过这事,汉武帝不也干过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也没能做到。真正的人,都是现实的人,人们研究历史都是有目的的,就是为现实服务。所以,存在古与今的张力问题,古为今用,这是少不了的。那么今呢,世界真是“一”吗?世界学术界就这一个是客观的吗?谁是客观的?自然科学可以说,历史学就不能这么说。
当我们这代人刚开始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时,都严重地感觉到,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承认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不承认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伟大意义。黑格尔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他主张“西欧中心论”,中国人看了,也是不能认同的。黑格尔不是代表世界精神,他是代表日耳曼精神。在他的史学观里,中国注定就是要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一个征服对象。
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历史证明,证明自己存在、生存的理由是必要的,否则就是自暴自弃。我们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是做了很多贡献的,对世界民族都有贡献。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历史是一个问题,从来需要多视角来看。苏东坡的诗《题西林壁》是这样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真正认识一个世界,怎么能只有一个视角呢?
我这是从消极意义上来看。我们从积极意义来看,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应该为更好的全面地看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吗?我们说人家“西方中心论”,你能责怪别人吗?你应该自己来说,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中国的地位、中国的作用,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是有责任的,是有使命的,要为中国说话,要向世界做贡献的。我们要贡献自己的角度,贡献自己的经验教训。(《历史科学》,有删节)
刘先生说的这些,可以说是他数十年学术研究、不断探索的思想结晶。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讲好自己的历史,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老一代历史学家的孜孜追求,也是中青年历史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寓真情于质朴之中
学术研究是一种理性思考,但是,这并不是说,学者可以不要情感,完全从情感中超脱出来。一方面,学者也是人,凡是人不可能没有情感;另一方面,情感是滋养人的精神的,学术史上许多名著都是饱含深情的呕心沥血之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是多么沉痛的慨叹,如果不是寄予深情,根本不可能创作完成这一巨著!在我看来,刘先生能取得如此杰出的学术成就,是与他对亲人、对老师、对学生、对朋友真挚的感情密切相关。正是这份真挚的感情,使他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之中,正所谓大爱成就大业。在刘先生的口述史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在南京成美学堂时,刘先生班上有一位同学,叫王永禄,是回族人,喜欢诗文,但自己不写诗,家里是开板鸭店的。临近毕业时,这位同学送他一本《白香词谱》,前面还题了一首词的上半阙:
聚散似春潮,虚无萍飘。他时相隔路迢迢。长恨愁多欢苦少,珍重今朝。
落款是:“王友敬赠”。刘先生以前就能背好多诗词,并开始创作。有了这本《白香词谱》后,他就掌握了写词的基本方法,长期受益。刘先生一直记得这位同学。20世纪80年代,他一次去南京出差,好不容易找到王永禄同学,可是他已经完全不认识刘先生。不管我怎么说,他都想不起来。刘先生回忆说:
那一回,我要是把这本书带去给他看,他看到自己写的字也许就能想起来。我心里觉得有点酸楚。他本来很有文人气质,很潇洒,可是为了谋生,他家开一个板鸭店,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当会计,一辈子当会计,把这样的事情都忘了。他写的字很秀气,“聚散似春潮”,“他时相别路迢迢。长恨愁多欢快少,珍重今朝。”这是《浪淘沙令》的上半阙。我也不知道这是他自己写的,还是抄别人的?如果是他自己写的话,那这个水平也是相当不错啊!可是,他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命运就是这样。(《难忘母校》)
王永禄是刘先生的中学同学,他们毕业以后一直再也没有见面,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刘先生仍然记得这位送他词谱的同学,在有限的时间里、在茫茫人海中费尽周折去找,这份真挚的感情恐怕不是常人所有的!顺便说一句,今年(2020年)元宵节,我在整理刘先生口述史稿时,正好整理到这一部分。为刘先生的这份情怀所感动,我为这首没有完成的词补写了下半阙,姑且作为一个纪念:
离恨实难消。红尘喧嚣。知音难觅际涯漂。物是人非情谊找,世事何遥。
对于曾经教育和指导过自己的老师,刘先生更是感恩在心。1955年,刘先生到东北师范大学进修。在离开北京前,他写了一篇涉及顾炎武《日知录》的文章,当时交给了白寿彝先生。后来,陈垣先生看到了,并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对此,刘先生一直心存感恩,并为自己当时没有去面谢陈老致谢而懊悔,这封信至今保存着。实际上,岂止是陈垣先生,从童年启蒙到已过鲐背之年,刘先生心中一直师恩难忘。在他的口述史中,有许多章节以老师为题,如《时霖先生》《汪海秋师》《“沈大代数”》《张宜先生》《张兰邨师》《钱宾四师》《冯振心师》《唐君毅师》《牟宗三师》《束世澂师》《唐至中师》《向往援庵》《柴德赓师》《林志纯师》《张正元师》《张天麟师》等,至于回忆老师的内容还远不止这些。
总之,通过《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刘家和先生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杰出的学术成就,还能了解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国现代学术史特别是中国现代世界史学科艰难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并且,通过刘先生的口述史,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学者的精神发育史,聪慧的天赋,真挚的情感,勤奋的态度,敏捷的思维,深刻的思想,谦虚的品格。其中供人借鉴和学习之处可以说比比皆是,诸如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学术方向的选择和学术研究的途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学术品格的形成和学术精神的培养等。可以说,阅读《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我们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精神滋养,而且是享受一场纯洁而又高尚的精神洗礼。
(本文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年12月。)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m.syxtk.com/wzzx/djhk/wypl/2021-08-24/70909.html-红色文化网

